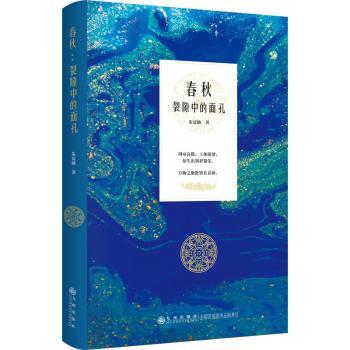内容简介
“溥天之下,莫非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臣。”周朝一统寰宇、睥睨天下的气象,到了春秋时期,已衰颓难见了。所可见的,是“臣”们的异心,是“土”的裂痕。一个个人物,在这裂隙之中行列而来:鲁隐公的温吞与犹疑,息夫人的智慧与隐忍,晋国谋士士蒍(士会的祖父)的谋算与洞见,周襄的短视与轻率……
这是诸侯竞相崛起、争霸中原的张狂岁月,侯将相、美人奇士,铁马的春秋时代有一种别样的繁盛。
目录
菟裘空梦
——鲁隐公未能抵达的远方
东门十年
——州吁,春秋时个弑君篡位的公子
齐大非耦
——太子忽的傲慢,与郑国夭折的霸业
敝笱在梁
——文姜:政治是女人能玩的游戏r style="color: rgb(102, 102, 102); font-family: tahoma, arial, "Microsoft YaHei", "Hiragino Sans GB", u5b8bu4f53, sans-serif; font-size: 14px; white-space: normal; background-color: rgb(255, 255, 255);"/>二子同舟
——一点手足的温情,一场亲情的阴谋
懿公好鹤
——卫文公,如何重建一个国家
庆父之难
——野心家的悲剧,在于权力的可望不可即
骊姬之乱
——谁是后的胜利者?
不共楚言
——息夫人的复仇,与楚国的野心
城濮之战
——真正的霸业,自战火中淬炼而
颓带荏祸
——驱虎吞狼,周室的尴尬与衰颓
蹇叔哭师
——崤山,秦穆公争霸中原的折戟之地
晋灵公不君
——赵盾,踏向专权之路
邲之战
——士会,晋国霸业得与失的见证者
赵氏孤儿
——繁华盛力反噬
尔虞我诈
——休战,是奢望r style="color: rgb(102, 102, 102); font-family: tahoma, arial, "Microsoft YaHei", "Hiragino Sans GB", u5b8bu4f53, sans-serif; font-size: 14px; white-space: normal; background-color: rgb(255, 255, 255);"/>申公巫臣
——可怕的复仇,是以天下大势为筹码
后 记
摘要与插图
菟裘空梦
——鲁隐公未能抵达的远方
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 (鲁隐公):“为其少故也,吾将授之矣。使营菟裘,吾将老焉。”
隐公十一年(前712),冬夜,鲁国。一阵兵刃相接的喧嚷声惊破了寂寥。
声音是从大夫寪a氏的家宅之中传来的。一伙歹人手持利刃,直奔国君息姑的住处。他们目标明确,动作迅捷娴熟,仿佛经过演练一般:他们早摸清了息姑的行踪,知道这一日他会离开宫室,知道他将入住寪氏家宅,也知道届时守卫薄弱,将是下手的好时机。
寒冷的夜色被刀剑点燃,敌意在一步步。息姑错愕中有些恍惚,仿佛再次回到了战场之上。
十多年前,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公子。那一日,鲁宋两国交战,他也在战场上奋力搏杀,突然地了一片昏暗与混沌之中。他围了,像是落入陷阱的猎物,只能束手擒。而后,他被送到了宋国大夫尹氏家中囚禁。
会如何处置自己呢?他惴惴不安。正是在这个地方,他遇见了钟巫。焦循在《春秋左传补疏》中说:“ 钟巫在郑为尹氏所主祭。” 这是尹氏所祭祀的家
神,尹氏俯首祭拜,恭顺而虔诚。息姑决定说服尹氏放自己走。为表诚意,息姑在钟巫的神像面前立下誓约:“若能助我回国,日后定将奉尹氏家神为自己的神主。”有神主见证,尹氏同意了,随他一同投奔了鲁国。
那大概是他离绝境的一次。是钟巫的庇佑自己才能化险为夷啊。他铭记于心,一直践行着当日的。今天,他也正是为了祭拜钟巫才选择了出宫。
钟巫神像所在的园子相去寪氏家不远,他住下,却不想给了歹人可趁之机。是他大意了,他忘了,世上的凶险之地,并不独独是战场。他再一次成了困兽,走投无路;而这一次,神主钟巫没能保护他。
味越来越浓。这些人比当年战场上的宋军更加可怕——他们似乎专为置他于死地而来。这次是真的逃不开了。
菟裘,他忽然想到了鲁国这个僻远的小邑——他为自己择选的隐居之所,自己本该在那里终老的。可惜一切都太迟了。
他闭上了眼睛。
│一、继位│
当人间后一丝亮光消失在眼前时,息姑看到的是弟弟允的脸孔。这张脸很陌生,此时他方惊觉,自己已没有认真看过这个弟弟了。当年那个羸弱的稚子原来早已长大成人。
他与允的纠葛,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在他成年时,父亲鲁惠公曾预备为他迎娶宋国国君的女儿。然而宋女鲁国后,惠公见其貌美,自纳之,令他另娶。宋女生下的是他的弟弟,是鲁国的太子,允。
父夺子媳,当时不算罕见。息姑什么都没有说,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若是有几分怅惘,更多的也是为父亲——是不是在父亲眼里,在任何的博弈之中,他都是无足轻重可被牺牲的那一个;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,当年他被宋国掳走后,并未寄希望于两国的交涉,而是选择了私下逃回。
是的,自己不是被偏爱的那个儿子,息姑很早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所以十一年前,当命运将他与允并置于命运的分岔口时,他甚感到了一丝受宠若惊。
公元前723年,鲁惠公去世,君位空缺,该由谁来继任,成了一道难题。按照惯例,自然是太子继位,但此时正值鲁宋两国频繁交战,而太子允年纪尚幼,无法担此重责——立幼主无助于振奋国威,而国本不稳必然影响前线。于是顺理成章地,作为庶长子的息姑成了候选人。
他年长,稳重,招致非议的是他的出身——庶出,这先天的缺陷使得他无法理直气壮地越过太子允去攫取君位。事实上,非议声也不时传入他的耳中。但这是他的机会了,战乱的局势与幼年的太子,共同为他铺了前往高权力的道路。如果放过,再也不会有了。
权衡之下,他做了个折中的决定息争议:太子年幼,我只好代为摄政;待太子长大,自然会归政于他。
我没有僭越,权力只是在自己这里过渡而已。他对自己说,对那些质疑的声音说。他看向身边的允,如此弱小,像是会长大一般。如果那真的到来了,我会交给他一个怎样的国家呢?
无论如何,息姑成为了鲁国国君,死后谥号“隐”。鲁惠公去世次年,公元前722年,即鲁隐公元年。《春秋》纪事自此而始。
作为鲁国第十四代国君,息姑继位于战乱之中,深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与破坏。他决心弥合这个伤口。
鲁国虽历史,此时却算不上强国。西周建立之初,将这片土地作为周公的封地,只是周公要留在周室辅,由其子伯禽代为赴任并建国。然而,鲁国“封土不过百里”,被周边林立的小国挤压,又有强大的齐国威慑,加之彪悍善战的夷狄不时侵扰,开疆辟土困难重重。与宋国的矛盾也多来自于此——两国相邻,实力又在伯仲之间。
尽管惠公晚年大败宋军,但息姑明白,战争的代价太大,一时的收益并不足以填补国内的损耗。既然无法压制对方,如此耗费下去,只能是两败俱伤。他决定为这场战争画上休止符,于是主动停战,与宋国在宿地结盟,两国自此开始友好往来。
选择停战的另一个现实需求,是来自齐郑两国联盟的压力。隐公三年(前720),齐国和郑国结成石屋之盟。齐是大国,郑是春秋初年崛起的新秀,两者的联合令的诸侯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。为了与之抗衡,很快,鲁宋两国重温宿之盟,约定互为援助。
面对与自己势均力敌甚更为强大的国家,若没有必胜的把握,维衡的局势是必要的。当然,息姑的作为不限于此。对不同的国家,他开展了灵活的外交政策。
莒国地处鲁国东侧, “ 莒虽小国, 东夷之雄者也”,面积虽小,实力却不弱。当齐鲁等国陷入内乱时,弱势方经常投奔这个的国家寻求庇护。后来的五霸之一齐桓公,早年投奔过此地,并留下了“勿忘在莒”的典故。这样的国家,必须要成为它的朋友而非敌人。为了加以笼络,息姑还颇费了一番心思,先将公室女儿嫁往与莒国关系密切的纪国,再以纪国为介,与莒国建立了联盟关系。
此外,息姑还主动与属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。如邾国只是一个子爵国,地位不高,而其国君邾仪父当时未受册封,连子爵都不是,但是息姑并没有因此轻慢于他,而是尊之重之,两国结盟;另一个属国戎国为东夷,主动前来示好,息姑也同样与之举行了盟会。
在这般苦心孤诣的联姻加结盟政策的运作之下,鲁国边境日趋安定,民生也渐渐回归于正轨。但是怀柔并不意味着没有獠牙,一旦有机会,鲁国也会积极地向外扩张,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。正如整个春秋时代所展现的那样,是权宜之计,战争才是常态。
隐公二年( 前7 2 1 ) , 鲁国发动了战争, “ ( 鲁国)司空无骇入极,费庈父胜之”。极国被灭,并入了鲁国的版图。那些尚未被吞并的国家,只是因为灭它们的成本太高才得以存在,而一旦受益远大于成本,战争在所难免。
│二、混战│
息姑很满意这种局势。后方稳固,鲁国在周边小国间暗暗渗透着影响力;与中原的其他国家则相互观望,维持着彼此间衡。
但这样衡很快被打破了。
裂隙先出现在了郑宋两国之间——郑国接纳了宋国的公子冯,这个宋殇公政治上的敌手。为了将公子冯控制在自己的手中,宋国挑起了战火。
隐公四年(前719),“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,围其东门,五日而还。”
被围困的郑国坚守不出,保存了实力,而在未来的日子里,它将用一次次的出征来雪洗这五日的耻辱;而雪洗之后,又是新一轮的报复。
东门之役,搅动了中原的风云,余波不断,很快齐、鲁、邾等国也都被卷入其中。一时之间,硝烟四起,铁蹄之声不绝。
战争的胜败并无定数,你来我往之中,各个诸侯国渐渐都倦怠了。而且各国国内的形势也时常生变,战争的走向更加难以预料。只是没有一个国家肯先停下来。这时,实力为强大的齐国站了出来,主持召开了瓦屋之盟,令宋、郑、卫三息旧怨。
这是隐公八年(前715)的事,离东门之役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。
瓦屋之盟开展得还算顺利。当使者将盟约的消息传达鲁国时,息姑真心诚意地颂扬了齐僖公的德业:齐君令三国冰释前嫌,令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,真是莫大德。
面对强大的国家,他懂得顺从;他也深知,这种拉锯式的战役,无法为任何一个国家带来胜利,息是再好不过的。
但是这依旧是暂时的。不久,郑、宋之间又起战争,瓦屋之盟破裂。而这次,鲁国放弃了盟友宋国,站到了郑国这边。
其实瓦屋之盟前,鲁宋两国已经有了嫌隙。当时宋国夺取鲁国的附属国邾国的土地,邾国又联合郑国伐宋,一直打到宋国外城,情势万分危急。作为宋国的盟国,息姑本已准备派遣援兵。可是当宋国的使者前来告急,息姑问起敌人的军队到达哪里之时,使者却说尚未到达国都。明明外城已破,前来求援还如此不坦诚。一怒之下,息姑拒绝了出兵,当然言辞说得很漂亮:本应与宋共担此危难,可是使者告知的情况与我所知不符,此作罢。当真是因为使者的辞令错漏吗?也许息姑只是不愿意在这场混战中陷得太深,故而以此为借口吧。
“入郛之役”,宋国颜面尽失,与鲁国的关系随之降冰点。
但鲁国似乎并不做此想——他想要宋国这个盟友,当然前提是自己处在的位置上。于是当瓦屋之盟郑宋讲和之后,息姑又亲自率领军队,讨伐邾国,声称是要替宋国报当年的“入郛”之仇。然而这番示好并没能消除宋国对其当日不出兵援助的怨恨。
瓦屋之盟破裂之后,宋国出兵,故意不告知鲁国,所谓的同盟名存实亡。于是息姑干脆断绝了与宋国的盟友关系,加入了郑国与齐国的阵营。此后,便是宋国的节节败退。
息姑,只站在胜利的一方。
│三、危机│
瓦屋之盟召开的这一年,息姑迎来了他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:隐公八年(前715),“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,以泰山之祊易许田。”
祊和许这两个地方各有其特殊的地位。《史记索隐》中道:“‘许田’许之田,鲁朝宿之邑。‘祊’者,郑所受助祭太山之汤沐邑。郑不能巡守,故以祊易许田,各从。”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中道:“祊者,郑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。许田乃鲁之朝宿之邑在上,诸侯不得以地相与。”
祊地为郑国所有,是用来祭祀泰山的专用田,在此起居、斋戒、沐浴。而许田许国,为鲁国所有,是鲁君朝见时的朝宿之邑。但无论归属哪个诸侯国,土地都所封,不得私下相与。现在,郑国借口郑而鲁,“祊易许田”,无疑是将抛在了一旁。
但这对鲁国而言,却有着更为的意义。“泰山岩岩,鲁邦所詹。”泰山在鲁国的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,而这次易地,无疑了泰山与鲁国的距离,令其祭祀之行更为顺遂。
息姑很高兴。他似乎没有意识到,郑国的强势背后,隐藏着诸侯争霸的风雨。而自己的处境,并没有比日渐落寞的要好多少。
自继位以来,息姑始终没能树立起作的。他身边,始终潜伏着一股疏离的势力,这股势力毫不避讳自己“不臣”之态。并非有反叛之心,只是不听从,不合作,游离在君权控制之外。而他对此,莫可奈何——他没有一支的心腹队伍可作依靠。
仅仅隐公元年(前722),息姑甫一即位,出现了三件“非公命”之事。
“费伯帅师城郎。不书,非公命也。”
“新作南门。不书,亦非公命也。”
“(郑)请师于邾。邾子使私于公子豫,豫请往,公弗许,遂行。及邾人、郑人盟于翼。不书,非公命也。”
“ 非公命”,即作为臣子却不听的命令而擅自行事,正是的极大蔑视乃忤逆。“不书”,指的是不见载于《春秋》。而《左传》将这些“不书”之事加以注释,也是表明了史家的批评与斥责。
在这股不受息姑控制的势力之中,气焰为嚣张的当属权臣公子羽父。
隐公四年(前719),宋、卫等诸侯国在围困郑国之后,想再次攻打郑国,“宋公使来乞师,公辞之。羽父请以师会之,公弗许,固请而行。”
息姑拒绝了宋国的出兵请求,而羽父却公然违抗了君命。“固请而行”四个字,更可见息姑的忍让与羽父的专横。但息姑不得不对他有所忌惮,因为这位权臣手中掌握着军队。
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,鲁国国力渐强,息姑也在逐步地将权力收归手中。时间很快来到了隐公十一年,息姑生命中的后一年。
这一年,他和羽父的君臣关系似乎走向了融洽,配合日益默契。滕侯、薛侯来鲁国朝拜,为先后的问题产生争执,息姑令羽父加息,一副君仁臣忠的模样。
同年,息姑频繁会见郑庄公,两国联合齐僖公攻打许国并获得了胜利。齐僖公将获得的许国土地让给息姑,息姑却送给了郑庄公,并说了一番漂亮的话:“因您说许国不交纳贡品,我才跟随讨伐;如今许国既已认罪,您的好意我不敢领受。”这番举措,为他同时赢得了齐郑两个强国的信任与支持。
一切都正在往更好的方向前行,他理想中那个强大的鲁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,而自己这些年的苦心经营,也将得到回报。但是令他猝不及防的是,这些很快戛然而止——十多年前埋下的隐患还是浮现了出来。而挖掘这个隐患并将之引爆的,。
这年的冬天,羽父郑重地向息姑提出了杀掉太子允的建议。作为老谋深算的权臣,他看到了息姑的能力。鲁国在变强,一同强大的,还有羽父手中的权力。他想要延续这样的君臣模式,更地说,想要在原来君臣模式中,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权力——他已拥有了兵权,现在,又盯上了主持内政的太宰之职。
羽父以为自己洞察了息姑的心思。虽然继位时,息姑声称只是代为摄政有一日会将权力交还给太子允,可确切是哪,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把握。十一年,是一段漫长的岁月。他已经熟悉了这个位子,这个位子,难道不会想再坐得久一些吗?当年的稚子已经成人,也不见他有何兑现诺言的动作。是啊,既然已经在这个位子上了,何不坐得更安心更安稳一些呢?没有比干掉对手更稳妥的法子了。息姑是这么想的,只是缺乏一点信心、缺乏一点动力而已。那么,不如由自己来推他一把。
于是羽父主动示好,表示自己愿意为息姑除去这个后顾之忧。但他的这番热诚迎来的是当头棒喝。息姑拒绝了,言辞和他继位时说的如出一辙,“为其少故也,吾将授之矣。使营菟裘,吾将老焉。”
│四、身死│
菟裘是鲁国边远的小邑,息姑想好了,等将君位交给太子允后,便在那里安置好田宅静地度过余下的岁月。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。
他应该是真心的,虽的权势诱人,但他一直是一个厚道、重信诺的人。他规矩地履行的职责,也真诚地对待着身边的人。
当年他在宋大夫尹氏家许诺,顺利回国后将祭祀其家神钟巫,他做到了;当日入郛之役,他因宋国使者谎报军情,怒而拒绝出兵,其中未必没有几分率与真切。
在位期间,他曾不顾大臣臧僖伯的劝诫,执意“如棠观鱼者”——去棠这个地方观看捕鱼——臧僖伯认为这有违礼法。数月后,臧僖伯去世,息姑想起此事,后悔,认为自己辜负了臧僖伯赤诚的忠心。为此,他特意将其葬礼在原来的规格上加了一级,以示悼念与褒扬。
他对名分之事也慎重以待。自己的母亲去世后,“不赴于诸侯,不反哭于寝,不祔于姑,故不曰薨。不称夫人,故不言葬,不书姓。”《春秋》上也只记载“君氏卒”。而对允的母亲,他则为她立庙并祭祀。因其是夫人,也是未来国君允的生母。
所以,他认为自己规行矩步,行事坦荡,问心无愧。然而他似乎真的忘了,权力的争夺本身是一场极为野蛮残酷的游戏。当那个骇人的建议说出口时,他与羽父都已经没有了退路,少羽父不会给他退路。他却以为什么都没有变,将此事想得过于幼稚与天真。于是才有了那,他如常出宫祭奠钟巫,毫无戒备。
没有退路的羽父其实也是被逼到了绝境上。他毕竟只是个臣子,若他日太子允登上君位,听闻他曾如言,他会是什么下场呢?遂当机立断,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转而密告允,称息姑有害他之心,不如早做准备,并表示愿为马前卒。
允心动了之位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,而这一步他已经等得太久了。这么多年,自己像个透明的人,隐匿在息姑的影子下。自己什么时候能摆脱这个影子呢?他不知道,也不敢问。现在机会来了,他不想在不确定上再等待下去了。况且这个位子,原本是自己的。
次月,冬夜,歹人攻破了大夫寪氏的家门。
息姑或许觉得自己有些冤枉,但他其实并非全然无辜。他似乎忘了前车之鉴,忘了周朝初建时,他的先祖周公也曾面临相似的处境,甚处境更为艰难。
公元前1043年,周武去世,当时灭商不久,局势未定,周成幼小,由武之弟周公代为摄政。而这引起了武其他几位弟弟管叔、蔡叔等人的不满。他们散布流言,说周公意图对成不轨。随后与商朝后裔武庚暗中勾结,起兵叛乱。周初的不少地方原本是商朝旧邑,闻讯也纷纷附和。
面对其他辅政大臣的疑虑,管、蔡等人以及商朝后裔的异心,周公果断地诛杀了管叔与武庚,放逐了蔡叔定了叛乱;在七年后,将一个安定有序的周朝交付给成,才地证实了自己的清白。
以周公的声望与才干,武去世后,他是适合代为摄政的人选。即便如此,当他“之位以治天下”时,依旧要遭受如此严重的猜疑及流言蜚语。千年后,杜甫的诗句“周公恐惧流言日”,并非虚言。而仅仅三百年后,他的子孙息姑却浑然不觉,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。
没有足够的威望,也缺少足够的魄力,甚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警惕心,息姑却妄想着自己能够全身而退。
如果,如果他能往前一步,果决狠辣一些,如羽父所言的那样铲除后患,铲除有异心的势力,未必不能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。又或者,他甘愿退让,能毫无回避、坦诚地与太子允交涉关于让位的事宜,也未尝不能取得谅解而避免手足相残的悲剧。
可惜历史没有如果。能力所限,格所限,他只能止步于此。
│五、尾声│
息姑死了。
寪氏成了替罪羊,也不过是做个象征的讨伐,后不了了之。谁是躲在幕后的那个人?所有人都心知肚明,只是无人敢去深究。
息姑被剥夺了作的尊严,甚没能以国君之礼下葬,谥号也只是一个尴尬的“隐”字。“不尸其位曰隐”,史笔暗讽他徒居其位而无突出作为。这对他显然是不的,保境安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也许他死都心怀理想与天真,畅想着能成一段兄友弟恭的佳话,但是世事岂能尽如人意。摄政十一年而不归政,原本脆弱的兄弟情,如何经得起这漫长的时间考验,如何能躲得过人心的猜疑与离间。
他不是周公,历史没能证明他的清白。
他没能去成菟裘,这场梦怕是永远也无法抵达了。